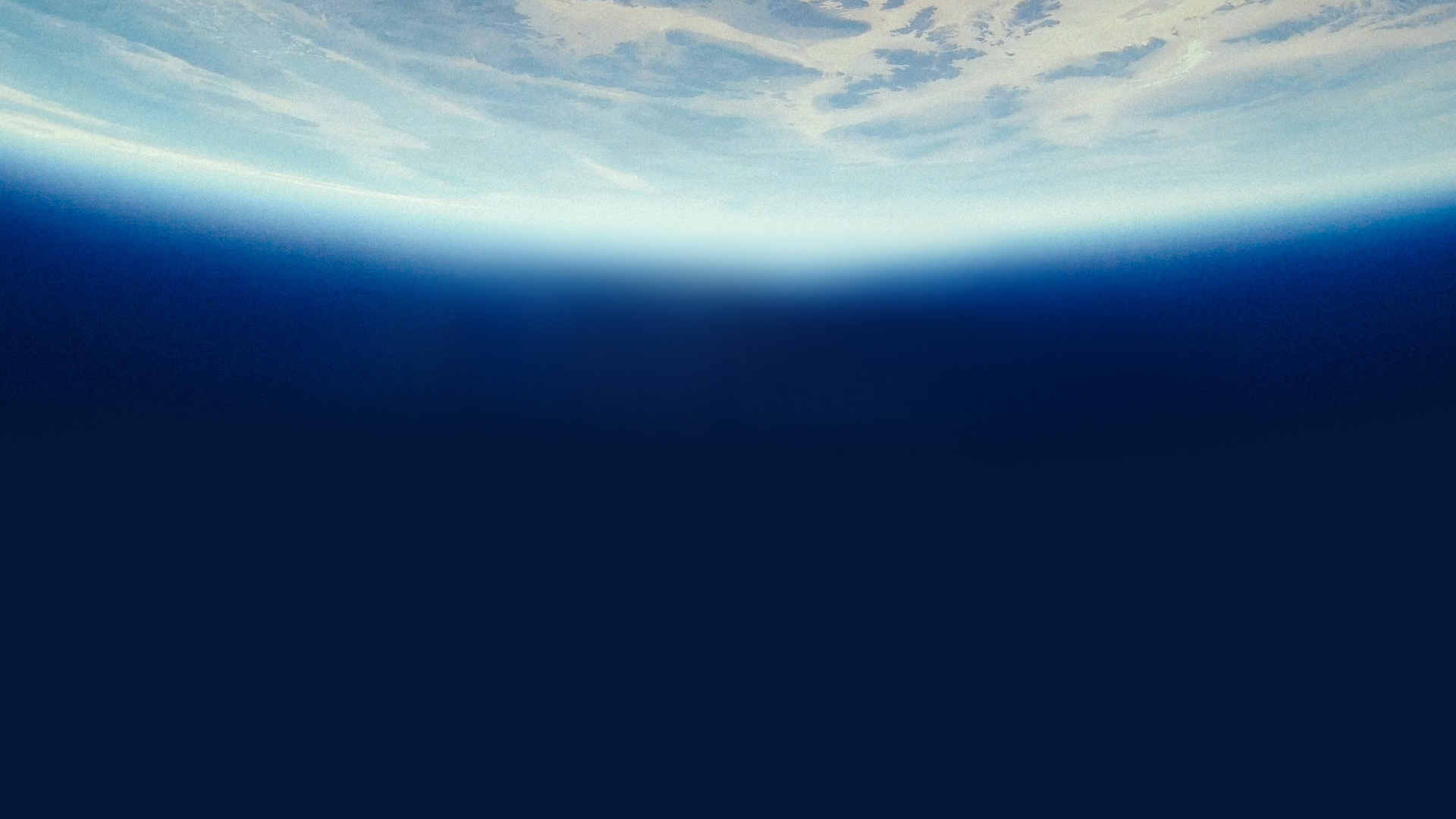丑闻如何塑造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的理解和实践?
责任创新杂志特殊的问题征文启事
关键的最后期限:2023年10月15日提交300字摘要。全文截止日期为2024年1月31日(详细的提交说明在本页末尾)
客座编辑和联系细节:
Joy Y. Zhang,英开云体育主頁(欢迎您)国肯特大学(开云体育app客服y.zhang - 20开云体育app客服3 @kent.ac.uk)
Kathleen Vogel,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美国(开云体育主頁(欢迎您)kathleen.vogel@asu.edu)
索尼娅·本·格拉姆-戈姆利,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开云体育主頁(欢迎您)sbenouag@gmu.edu)
特刊的范围
科学丑闻对我们理解和实践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RRI)尤为重要。人们普遍认为,研究丑闻在动摇科学体系方面最为重要(Robaey, 2014),人们也普遍认识到,研究不端行为的频率正在上升(Fanelli 2009, Drenth, 2010, Kornfeld和Sandra, 2016, O 'Gardy, 2021, Roy和Edwards, 2023)。然而,缺乏系统的研究如何不负责任的研究活动影响了治理和科学规范等等如何我们应该负责任和有效地与丑闻或丑闻的个人接触,以告知未来(Vinck, 2010, Owen, Macnaghten和Stilgoe, 2012, Meyer, 2022)。本期特刊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我们邀请对丑闻和RRI的相互影响进行实证和概念严谨的调查。
丑闻是公开的违反道德或法律规范,引起公众的强烈抗议(Adut, 2008)。因此,它们至少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为RRI提供了最多的信息。从系统结构的角度来看,丑闻暴露了现有法律配置与知识生产背后的复杂性之间的不匹配。实证研究表明,科学家不会盲目地服从一种话语,而是“购买”或积极培养能够适应其研究议程的社会政治环境(Russo, 2005)。这种“购物”的倾向随着东方的崛起而进一步成为可能。在对印度和日本的研究中,sleboom - faulkner(2019: 372)发现,当个别科学从业者充当组织国际合作的中介时,他们也充当了“监管经纪人”,将他们关于不同监管制度的地理知识转化为(科学和经济上)有利可图的“监管资本”。此外,公众对丑闻的监督并不局限于追究个人的责任。相反,丑闻往往导致识别(并可能纠正)嵌入现代官僚机构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Beck, 1992,1999, Giddens, 1999)。上世纪90年代英国的疯牛病危机和艾米·莫兰-托马斯(Amy Moran-Thomas)暴露脉搏测定者种族偏见的经历就是这样的例子(Levidow, 1999, Moran-Thomas, 2020)。
从文化规范性的角度来看,科学争议对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规范性和合法性的一些制度提出了质疑(Martin和Turkmendag, 2021)。社会不断寻求新技术的可能性与他们的愿望和抱负之间的一致性。以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组编辑为例,一方面,操纵我们遗传条件的新方法使我们对什么是合理的需求或合理的福利有了新的理解。另一方面,它可能同时关闭人类的可能性(例如,“体外优生学”和基因决定论的复兴),并使旧的权力关系永久化。文化规范的演变不仅仅是由技术进步驱动的,因为它也与各种利益相关者发起的话语和制度变革密切相关。丑闻的实例和随后的社会反应可以提供深刻的机会来探索认知革命如何从各种来源产生,以及它们有时如何伴随着内在的矛盾。“理性的”技术进步可能不被视为“合理的”或社会合法的(Irwin and Wynne, 1996; Jasanoff, 2004; Miller, 2008)。它们还迫使我们重新考虑“边界工作”(Gieryn, 1983,1999),不仅在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科学之间,而且在专业和非专业从业者之间的传统边界(见Zhang和Datta Burton, 2022)。
更重要的是,丑闻代表了一种认知上的开放,它揭示了当代研究和创新背后隐藏的社会过程和特殊利益,否则这些就不为公众所知(Scott, Richards和Martin, 1990, Nelkin, 1979, Kaiser, 2022)。需要提醒的是,创新研究本身并不是一套原则,而是一系列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和科学利益相关者对“创新过程及其可销售产品的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可取性”进行审议(von Schomberg, 2011: 9)。创新研究的发展是议程和社区的扩展,使这些审议得以延续和过渡(De Freitas和Pietrobon, 2010, Stephens和Dimond, 2016)。可以说,黄禹锡的干细胞丑闻重新唤起了全球对民族主义和父权结构对科学的有害影响的警觉(Gottweis和Kim, 2010)。正是贺建奎的CRISPR婴儿丑闻和随后的比特币资助的设计婴儿项目,引起了全世界对新型研究型创业能力的关注(Zhang和Datta Burton, 2022)。
但丑闻与RRI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近年来,出现了两波科学不端行为。第一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导致行政部门关注公众参与科学和“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ELSI)(见Engelhardt and Caplan, 1987; Nelkin, 1979; Bucci and Carafoli, 2022a)。这也导致了RRI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框架的提出(Griessler et al., 2023)。第二波浪潮通常被认为是从新千年开始的(Montgomery and Oliver, 2009, Wible, 2016)。电子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对撤稿的系统跟踪和对科学不端行为的调查。因此,第二波不仅包括高调的案例,而且其特点是在更大范围内发现不负责任的研究行为(Wible, 2016)。然而,与第二波浪潮相关的三种关键的矛盾心理,我们希望这期特刊能够更多地阐明。
首先,似乎有一个悖论,在一个科学诚信和声誉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前沿研究和创新变得越来越容易丑闻(德伦斯,2010年,罗伊和爱德华兹,2023年)。一项针对11647名研究人员的调查显示,2%的研究人员在其职业生涯中至少有过一次不当行为(Fanelli, 2009)。在这些研究领域中,复制结果存在天然障碍(例如:实验设置的复杂性,或生物可变性)特别容易产生欺诈行为和争议,正如Fleischmann-Pons关于冷聚变和实验生物医学的主张(见Eastwood et al., 1996, Ritter, 2016, Wible, 2016, Bucci和Carafoli, 2022b)。一些人警告说,除非发生更系统的变化,否则当代学术界很容易受到“不负责任的研究完美风暴”的影响(Aguinis, Archibold和Rice, 2022; Bucci和Carafoli, 2022b)。
解开“承担责任”和“不负责任”的过程同样重要,它们不一定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Meyer, 2022)。对丑闻兴起的一种常见解释是通过“学术资本主义”的视角(Hoffman, 2011)。也就是说,知识的逐步私有化和以利润为导向的学术出版导致了默顿科学规范被市场心态所取代(Hoffman, 2011; Singh Chawla, 2021)。其他人则认为,发展中国家、自由的研究体制和不自由的实验室文化的结合,使亚洲国家特别容易受到可疑行为的影响(Lee和Schrank, 2010)。但并非所有的不当行为和争议都是“丑闻”。例如,学术期刊公布由于捏造、伪造和抄袭而撤回的论文,提高了公众对科研界自我监管能力的信心。但贺建奎非法应用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构成了丑闻,不仅仅是因为它公然违反了生物伦理和法律法规,也因为它的临床必要性和科学有效性仍然存在争议。正是中国不透明的政治文化和何氏跨国“信任圈”网络的曝光,使得这一案件尤其令人反感(Zhang and Datta Burton, 2022)。也就是说,震惊世界并继续引起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疯狂,还有纵容和鼓励这种错误行为的行为。换句话说,使可疑的研究行为特别应受谴责和具有破坏性的是高度依赖于上下文的(von Schomberg, 2015)。 Yet key questions on how actors and resources are mobilized to effectively counter-act mainstream research ethics remain under-explored.
其次,有必要批判性地审视丑闻是如何(以及是否)给研究实践及其治理带来变化的。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许多新的研究疏忽是一个问题响应20世纪下半叶科学不端行为的日益公开化(Montgomery and Oliver, 2009, drancy, 2010)。个人的成功,例如血清学家Nancy Olivieri在1996年揭发Apotex的临床试验,也表明丑闻的曝光有可能在学术期刊和研究机构中促成政策变化(Schafer, 2007)。但另一方面,丑闻可能并不总能引发监管部门的反应,甚至引发必要的讨论。现有的生物医学丑闻研究表明,有时个人或公司可以“简单地顶住”批评(佩洛西,2019年,428年,西斯蒙多,2021年)。对单一案例的关注可能会将其他发展问题留在幕后,并转移对其他监管挑战的注意力(Prainsack, Geesink和Franklin, 2008)。虽然机构对科学不端行为的检测越来越透明,但如何处理这些不当行为仍然不透明(Hesselmann et al., 2017, Hesselmann and Reinhart, 2021)。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限制未来的不当行为,我们就必须更加批判和反思“对没有改变的事情保持相当大的沉默”,以及影响研究丑闻不可见的权力制度(Prainsack, Geesink和Franklin, 2008: 355)。
第三,与此相关的是,随着科学组织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它要求我们对如何能够和应该参与科学丑闻进行新的反思,以更好地为未来的实践提供信息或澄清公众的疑虑(De Freitas和Pietrobon, 2010)。对第一波科学争议的研究已经质疑了传统的“对称”参与的有效性,并警告学者在调查不当行为时要更多地反思自己的立场(Martin, 2015, Sarda, 2011, Scott, Richards和Martin, 1990)。正如帕姆·斯科特及其同事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从事研究和理解丑闻的社会科学家必然是“争议的俘虏”(斯科特,理查兹和马丁,1990:475-6)。这并不是要抹黑社会调查的反思性和专业性,而是要强调,对丑闻的社会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融入到对丑闻的社会认知和反应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是他们研究的争议的“俘虏”。因此,为了负责任地参与丑闻,需要研究人员更加意识到,当他们对丑闻的研究在不知不觉中延续或加剧误解时,他们的研究也可能看起来是丑闻(Scott, Richards和Martin, 1990,491, Martin, 2015, Sarda, 2011)。
然而,许多因素使得对科学丑闻进行负责任和有效的研究更具挑战性。首先,当代“取消文化”和不断扩大的意识形态分歧是对有争议话题进行公开和坦率对话的新障碍(Meyer, 2017)。例如,本期特刊的特邀编辑在2023年初组织了一场与名誉扫地的研究员贺建奎的公开讨论,却遭到了媒体和学术同行毫无根据的批评,指责他们为贺建奎平反,粉饰中国,玷污了生物伦理和生物治理领域的声誉(Zhang et al, 2023)。我们鼓励更多中国学者解决监管缺口的主要目标,一再被这些批评撇在一边。然而,正是对参与有争议的案件和个人的审查,使得贺建奎有问题的研究项目不受限制和质疑。此外,对丑闻和不当行为的讨论也会产生其他影响,这不利于在RRI上形成团结,并可能使我们看不到监管空白。例如,现有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对某些文化的(无意识的)偏见和“穆罕默德·阿里效应”,在这种效应中,研究人员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诚实、更有道德责任感(Fanelli, 2009; Hesselmann, 2009; Dimond, Lewis and Sumner, 2023)。对中国和印度科学崛起的研究表明,观察到的许多监管和执法差距并不一定源于文化差异。相反,由于其研究发展的范围和速度,这两个国家对全球共享的许多棘手问题都具有放大镜效应(Zhang和Datta Burton, 2022)。因此,许多人强调了处理丑闻和科学政策的“非殖民化”紧迫性(Hesselmann, 2019, Zhang, 2023)。 Finally, we need to re-think how we generalize lessons learnt from scandals. To be sure, each scandal is unique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infused with personality, localized research culture, socio-political particularities and a specific technical context. This is further complicated by the fact that we are in an era of ‘post-academic science’ (Ziman, 2000), in whic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ocietal funding has given rise to a multiplicity of new configurations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s that cut-cross nation-state an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Critical events such scandals can nevertheless serve as reference points and shed light on general patterns for governance. However, we may need new praxis to guide us on to what lessons can be generalized and within what scope.
我们邀请完整的研究文章(6000至10000字,包括参考文献,尾注)和观点文章(2000字),涉及但不限于以下一个或多个主题:
- 科学丑闻以什么方式告知或改变我们对RRI及其治理的理解?丑闻何时以及为何不能促成变革?
- 为什么丑闻在当代科学中似乎更频繁?它说明了当代研究和治理实践的本质是什么?
- 是什么条件(如文化、政治或结构)使科学争论或不当行为成为“丑闻”?
- 政策制定者或监管者为什么要关心科学丑闻?研究科学丑闻或丑闻个人对国家、地区或全球治理的价值是什么?
- 在研究丑闻和随后的科学-社会和/或科学-政治关系的公共辩论中,社会科学家的作用是什么?
- 什么构成了对科学丑闻进行“负责任的”社会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组织这些研究,如何传达研究结果,同时对不同的公众保持敏感?
- 在识别和分析科学丑闻以为政策提供信息方面,有哪些新的方法创新?我们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从个人(通常是高度情境化的)案例的研究中获得见解,以告知未来的治理(跨越不同的背景)?
- 怎样才能使对科学丑闻的研究不负责任或无效?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避免科学丑闻的社会揭露本身成为“丑闻”?
- 我们应该如何向公众传达科学丑闻及其反应?需要沟通什么,在什么时候,由谁来沟通?公众应该如何参与处理科学丑闻?
- 我们怎样才能防止一个科学丑闻事件引起关注,使公众的注意力从与技术进步有关的更重要或更紧迫的话题上转移开来?或者,如何利用科学丑闻来进一步关注那些未能引起关注的重要政策/治理问题。
提交说明
请在2023年10月15日前将摘要(300字)直接提交给特邀编辑。被录用者将被邀请提交一篇完整的论文。论文全文应该是提交日期:2024年1月31日提交门户.请在投稿时注明您希望入选本期特刊。被录用的论文将立即在网上发表。请按日记的顺序来作者须知
的责任创新杂志2021年的指标包括:3.370影响因子,影响因子最佳四分位数,最佳四分位数.JRI的年下载量/浏览量为18.7万。作为一份完全开放获取的期刊,JRI可以为来自欧洲和北美以外的作者以及来自任何国家的早期职业研究人员的主要作者提供有限数量的文章处理费减免。了解更多关于文章的信息发行费用和资金选择.
全文参考书目可在此下载:
https://blogs.开云体育app客服kent.ac.uk/global-science-and-epistemic-justice/files/2023/05/Full-Bibliography.pdf